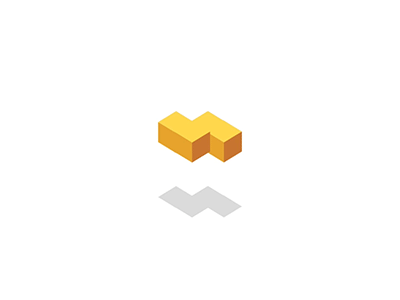对于传教士和中国教育的关系,基督教内外都有过探讨。近期,“历史百人会”平台发起了一场“传教士与百年中国的往事”线上研讨会,在传教士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及医疗事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其中谈到了伯格里和石门坎、苏慧廉与温州,以及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等话题。
北大教授陈浩武大量关注伯格里牧师和石门坎的故事。他首先介绍道,伯格理是在贵州毕节威宁县石门坎乡活动的一位传教士,他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这个文字的今天被称为花苗文。此外,伯格理运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就是花苗文《圣经》。伯格理运用花苗文《圣经》来传教,同时用这种文字帮助苗族人发展教育,办学校。
在伯格理去石门坎之前,能简单数字运算的苗人屈指可数,只能依赖会简单加减乘除的老人,可见教育水平极低。但伯格理之后,至1949年之前,他们先后办了120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苗族精英。
如何用信仰和文化改变一个地区?陈教授指出,即使是石门坎这么落后的地区,只要把教育文明、信仰这些元素嵌进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伯格理事件给我们的现实意义。
此外,主持人方韶毅以及《寻找苏慧廉》的作者沈迦谈到了苏慧廉、曹雅直于温州传教、创办教育的故事。苏慧廉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光绪七年(1881)飘洋过海来到温州,在温州传教二十六年,把整个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苏慧廉在温州创办了西式医院和学校。
还有一位传教士曹雅直先苏慧廉来温州,同样创办了西式学校。可以说是这些传教士改变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其他传教士所到之处无一不如此。温州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信徒众多”,是和曹雅直、苏慧廉他们所奠定基础有极大关系。
此外,也有人谈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发展史。开始,基督教青年会格林等人在天津创办了现代学校,给南开的创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而南开的课程设置比如体育课,都是模仿青年会学校做的,且外聘了很多青年会工作人员担任教师,他们带来先进的教育和办学理念。南开校长张伯苓也是一名基督徒,和司徒雷登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张伯苓不主张把信仰教育带到学校里来,但他个人的言传身教和身边基督徒的典范作用在南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讨论中还提到,早期在华北一带举办的运动会,首先都是青年会倡导的。后来南开进行了模仿和联合,越做越好。南开体育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也很密切。比如南开后来出现的一些体育人物,原来都是在青年会服务的。
有人谈到,从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为上帝的仆人来到中国,为了宣教而宣教,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早期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效果都不太理想。于是在传教士内部逐渐产生了分野,一部分传教士发现借助教育来宣教,效果要好得多,于是教会学校逐渐在中国兴起。早期的教会学校,并不十分重视教育,教育只是宣教的一种手段,在那一时期的学校里,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学生也多来自宗教家庭,或贫寒子弟,因为当时的教会学校不仅教授知识,还能管饭给钱而且还能安排工作。但是到了司徒雷登这一代传教士又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觉得过去的传教方式僵化,效果不好,所以釆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以司徒为代表的这一代开明传教士教育家开始不再硬性要求学生们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再要学生皈依宗教后,教会大学一步步融入中国的世俗社会,也更贴近教育的本质。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此时期教会大学的宗教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尽管不再硬性要求学生们皈依,但却让更多的人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使宗教与教育二者相得益彰。
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大学教育,传教士在中小学基础教育这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最近几年流行民国教科书,教会学校编的教科书就不被重视,其实他们当时编的英文教材很有价值,编写者不乏哈佛牛津高材生。
在讨论当中,与会者指出需要客观的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贡献。过去对传教士基本是全面否定,而随着社会的变化,传教士又开始由被妖魔化转而被圣徒化,这都不尽客观。
注:历史百人会由国内外历史同好共同发起,旨在砥砺学问,共享史学信息。百人会以公益性、学术性为原则,以微信公共账号“历史百人会”为发声平台。不定期组织讲座、内部研讨会和历史论坛等研究活动。本期为其线上第二期研讨会。
原文链接:历史百人会线上学术沙龙第二期:传教士与百年中国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