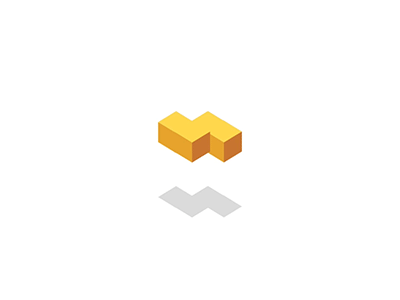【歌2:2】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与相忱出狱的同时,王明道先生也被释放。一九八0年一月,王先生回到上海后不久,就给相忱写来了一封信。当时王先生的眼睛还未失明,尚能勉强写字,但字体写得很大,一共写了六页。王先生在信中首先向相忱认罪,承认自己在监狱里撒谎了,使很多人因为他的软弱而跌倒;随后,王先生又写到:“我有件事情提醒你,倪柝声也撒谎了,不能听他的……他的品行不端正,千万别上他的当。”相忱把这封信看了两遍,又拿给我看。对于王先生在信里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相忱的态度是:“人都是软弱的,不能抓住人家不放。 人犯错误是正常现象,悔改了就是好的。《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对于第二个关于倪柝声弟兄的问题,相忱很不以为然,和王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他(指倪拆声弟兄)犯罪,我也没看见,我不能说,我不能跟着他(指王明道先生)说。我没看见他犯罪,那可能是人家造的谣,不一定就是真的,所以我不说。他(指倪拆声弟兄)是神重用过的,我不说,不批评他。”对于一些对待别人的错误过于热衷的人,相忱一贯的立场是“人家的事,你干吗那么费劲啊?将来他自己要向神交帐的。”相忱的回信没有给我看,也没有对我说,不知道他是怎样回答王先生的。因为我从来不主动要求查看相忱的来往信件,只有他拿给我看,或者讲给我听。
王明道先生和相忱当年一同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王先生是以“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的名义获释,而相忱是“维持原判”,只是出于符合“年龄六十岁以上,在监服刑超过二十年。”的条件,获得假释的。假释之后还有十年的考验期,考验期内没有公民权,一切要由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监管。因此相忱必须要定期向派出所上交思想汇报。开始时派出所要求相忱每两个星期交一次汇报,以后逐渐放宽到一个月、半年交一次。到了该交汇报的时候,我就从外面给相忱带回来两本最新的《半月谈》,让他照着上面的宣传口径抄写几段,好在相忱在监狱里常写这类汇报,在这方面也算是轻车熟路了。至于汇报的内容不外乎就是那几条,第一是汇报自己的学习“每天听广播,看报纸”;第二是汇报个人的行动“我爱人上班,我在家里做饭”;最后是:“请求所长帮助我,尽快获得公民权”。每次汇报交上去,所长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写来写去,就是这些内容,再写还是这些内容,后来派出所就不要了,只到年底写一次就算了。但是,相忱的考验期却一天不少地延续了整整十个年头。
考验期内的人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行动自由,若要离开居住地必须预先征得派出所的批准。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考验期结束后,相忱和我马上去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十月底,我们坐火车到达上海,陈本伟弟兄来车站接我们,一见面,陈弟兄就告诉我们:“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我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我们临时改变原先打算住在陈本伟弟兄家的计划,直接赶到王先生位于武康路的家里。
虽然这时王先主已经年届九旬,身体衰弱,眼睛也已完全失明了,但还是在王师母的搀扶下,到门口迎候我们。他拉住相忱的手,哭着说:“相忱啊,我的好弟兄!我看不见你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不住地抚摸着相忱。屋里的人也都哭了。王师母说:“你们的身体还这么好,还这么年轻,大好了!快坐下吧,快坐下吧。”相忱和王先生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彼此讲述着这些年里各自的经历。相忱回顾自己,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平平常常,啥也不啥。整天忙。也想不起写点儿什么,没什么著作。”王先生打断相忱的话,说:“你别这么想!没有著作不要紧,有忠心就够了!神是看你的忠心,至死忠心到底,必得生命的冠冕”。(启2:10)原本上了年纪的人就易于怀旧,特别是看到相忱和我从北京来,就更唤起了王先生对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和他在甘雨胡同故居的思念之情,同我们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难免有些伤感。
王先生在上海武康路的住宅是他儿子王天铎单位分配的。吃饭的时候,天铎也来了。天铎对父母很孝顺,每星期都要两次回来陪父母吃饭。他和我们不太熟悉,但见面还是很恭敬地你呼我们“叔、婶”。谢饭祷告时,我们轮流开口祷告,我没睁眼,不知道天铎祷告了没有,可是没有听见过他开口。吃饭中间,王师母对他说:“你十二岁就受了洗,现在你却不承认主,有你这样的吗?”但天铎不吭声。相忱也问他:“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老,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铎想了半天,才开口说出:“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而后,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创世纪》。显然天铎虽说表面上对我们很是客气,却在回避和相忱作深入的交谈。天铎此时担任着上海市人大代表,又是上海市政府的参事,还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联合国召开的专业会议。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和宋天真的丈夫王恩庆是好朋友,听说王恩庆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曾作为“进步学生”的代表,秘密地赴“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来之后他的个人信仰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铎的动摇就是受到了王的影响。王恩庆后来虽也成为知名的学者,但他在去世之前,曾指着自己满满一屋子的书,亲口对我说:“我岳父为主传道,我却没有学习他!我会五国外语,读了这么多的书,可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后悔莫及啊!”相忱认为天铎是属于流浪在外的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相信神的儿子迟早会归回的。
王先生、王师母和我们在一起,主要谈的都是回忆以往的人和事。回忆他当年悉心培养过的两个传道人,一个是姓罗的,后来去了美国却是灵性下沉,放弃了信仰,不再为主传道:另一个就是彭鸿亮,彭很年轻,比相忱还小十多岁,当年他的讲道处处模仿王先生的语气和动作,因此,人称“小王明道”。据说他在被捕后,检举了包括相忱在内的很多人,把他自己提议发明信片召集人到王先生会堂聚会的事完全推到相忱的身上,所以他监狱里只呆了一年多就被放了出来。可他最后的光景却很不好,出狱后就患上了半身不遂。听杨润民先生的女儿告诉我,她在东大地桥亲眼见到彭鸿亮,脚搓着地走路,不停地流着口水,话也说不清楚。一九六二年就去世了。又回忆起当年曾在他的会堂聚会过的那十一位传道人,他们中间既有已经为主殉道的武文蔚牧师和张周新、陈善理夫妇;也有先后参加了“三自会”的毕咏琴和王镇、吴慕迦、刘秀瑾等人,这几个人虽也曾和我们一同受苦,但后来的道路却不同,还有未曾被捕的杨润民先生。杨先生带领的南城布道所是基督徒会堂的一个支堂,他有八个孩子,家里开销大,就过于计较王先生给他的供应,对王先生很有意见。还回忆起他曾经的亲密同工,同时也作过相忱老师的石天民先生和王克忱先生。王先生还专门向我们了询问了几位他早年的同工的情况,我记得其中有曾在基督徒会堂担任过执事的张庆生弟兄。张弟兄对王先生十分推崇,曾经把自己经营烟火工厂的所得大量奉献出来,用于支持王先生的主工。后来他被定为"资本家",受到残酷迫害,这时已经不在世了。王先生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言语表达时而清楚,时而模糊,耳朵也聋,对他说话要很大声才能听得到。相比王师母一的头脑更清楚一些,对有些事情和年代比王先生记得更准确。
我们在王先生家里参加了一次主日的聚会,聚会的人不少,有一百多人,三间屋子坐得满满的,可是王先生的讲道的确显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相忱还独自去探望了李天恩弟兄,因为李弟兄曾来过白塔寺教会一次,所以这次是特意回访他。四天过去了,能说的往事都说得差不多了,再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决定告辞。临走时,王先生对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流着泪,拉住相忱的手,说:你们多住些日子吧!你们多住些日子吧!"相忱询问王先生:"你对我还有什么劝勉,有什么指示的?"王先生摸索着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交到相忱的手里,上面写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几个字,是王先生亲自用墨笔书写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相忱把这张纸条拿给曾是王先生会堂同工的黄道安弟兄看,黄弟兄告诉我们,王先生所写的这八个字出自《诗经•大雅•荡》,原意是指做人做事大都有一个开局,却很少有能够到达终点。王先生引用这句古诗的用意在于,既是勉励相忱,也是勉励所有在主里的同工同道,要众人在事奉神的工作上,既有了好的开始,还要用自己的一生为主打美好的仗,竭力把起初从主所领受的真道,持守到底。同时,王明道先生也是在藉此表达自己务要为主尽忠的愿望。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明道先生终于息了他在地上的王作,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了。接到消息的当天,相忱就准备即刻动身赶去上海。可是随后又有消息传来,说因为这天正好是主日,王先生是在聚会中间去世的,于是正在进行的敬拜聚会当场改成了追思会,此外没有另外举行什么。由于上海当时天气炎热,王先生的遗体在当天下午就匆匆被火化。相忱只得取消了自己的行程。稍后,相忱写就了《记神仆王明道先生》一文,作为对王先生的记念。
又过了八个月,王师母刘景文姊妹也安息主怀。我们是事后才得到通知的,故而也没能去参加她的追思会。从上海寄来的照片里,我看到追思会的横幅上写的是“刘景文丧事聚会”。我心里因此非常难过,不理解他们怎么能把一位圣徒的去世看作是“丧事”。我们是在主基督里得有永远生命的圣徒,我们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是进入主的乐园当中,等待主再来的那天,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要复活,在永生神的荣耀国度里永永远远与她同在。这是何等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