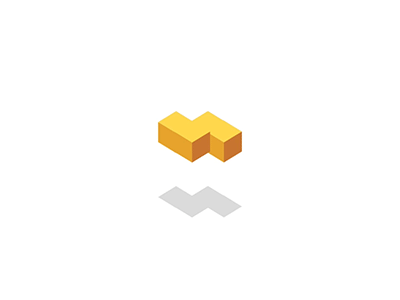编者按: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188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英国作家、记者。1909年至1910年间,丁乐梅徒步穿越中国,并在云南记录了苗人在柏格理等人的帮助下取得的文明成果。
苗族分布广泛,单我们知道的聚居地便有不少。他们的真正的家园其实位于贵州,而古时他们的足迹大概已经远至湖南,目前上述省份的汉人的血管里,毫无疑问地流着不少苗族的血。相较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是新近才来到云南的,但正逐步向西扩张,越走越远,而且仍然沿用着自己的语言、服装与风俗。据我个人观察,他们在西面的分布,已经延伸至了大理府三十英里开外、稍稍偏离主干道一点点的地方;但戴维斯少校发现他们直到西藏边境仍有出没。他说:“我所发现的最西端应是在多牛(纬度23°40',经度 98°45')。似乎整个云南中部和北部都没有他们的踪影,但一路向北,又在四川西部重新出现,在雅砻江流域(纬度28°15',经度101°40')有几个村子。”
少校显然没有注意到位于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府苗族聚居区。从昭通府出发,顺着通往东川府的道路走上三天,在某条朝北的支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苗族的村子;然后,从东川府出发,沿西北方向再走三天,我们又来到了位于龙吟山的苗寨;再然后,朝西南进发,穿过某个绝对从未有人勘测过的乡间地带,又找到了洒普山。上述提到的这最后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内地会的总部,若按照目前的进度,哪怕是保守估计,二十年内也会有不少于一万人收到基督的箴言。当然他们并不都是苗族;除苗族外也有怒族、傈僳族,还有其他很多我们目前仍未了解到的部族。
因此可以看出,从首府云南府出发,沿着主干道的两个方向,都可以通往位于叙府下方的长江分流处。在金沙江与贵州边界之间的狭长地带,可以经常看到苗族。然后,在江对岸的四川省,又能发现他们。接下来,继续向西直至贵州,我们就找到了他们真正的家。
尽管苗地与马来西亚相去甚远,但是我与苗族人接触越多,就越能从他们的日常习俗及性格特点中发掘出他们与马来人和萨凯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人是居住在马来半岛原始丛林中的山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民族学者或许会嘲笑这个猜测——正如我在苗族人中住过一阵子后,也开始嘲笑那些没住过的人写下的东西。
这一区域有两条苗族的主要分支——
1. 花苗族(或白苗族)
2. 黑苗族
后者被认为是两个族群中较为高等的,说不同的方言,行为方式、穿着打扮也有或多或少有些不一样,若要研究这一课题,得用一生时间来阅读永无止境的冗长论文,方才能稍微开窍。希望了解苗族种内差异的人,可以参考克拉克先生的《贵州与云南》,亨利·奥尔良亲王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以及巴博尔先生的作品。
戴维斯少校也提供了些许山区居民的相关新信息,他所说的大体正确;不过在他的书以及所有这一主题的相关书籍中,语言测试的结果均相差较大。例如在昭通及周边地区,倘若旅客使用少校编译出的词汇,根本寸步难行。我完全无法将之与当地居民的口语相对应,因此附上了一张表格来指出语音上的差异(我做这件事时心中真的满怀对戴维斯少校的尊敬)。多说一句,我这张表格是我从云南东南部采集到的语言,戴维斯那张则取自他的书的第339页。他说他所给出的词并非与口袋本苗族词汇中的每一条都符合,有一些取自其他苗族方言!然而,二者的对比非常有趣。
直到一两年前,苗族仍然只有口语;从未有人写过字,也从未有人曾经幻想过语言竟然还能被写出来。在伟大的苗族复兴期间,数千名苗族人突然来到昭通府的传教点,请求传教士们到寨子里去教他们,到那时他们才发现语言至少得写出来。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里塞缪尔·柏格理牧师的肩上,他被认为是云南东北部基督教运动的先锋。然而,由于苗语有“音调”,所以它很难被付诸文字,行动因此陷入了空前困境——所有中文学习者都知道,音调可是恶魔的发明——由于音素的数量太少,并不足以将意思传达清楚,所以每个发音都被赋予了不同的音调。这就好像用驾驭音乐的方式来支配语言:一个人不仅要记住所有他想说的词汇的发音,同时也得记住它们的音调。鉴于苗族人从未适应过学习,所以推广者认为他们的文字应当尽可能简单,因此他们希望能发掘出一个能使这些愚笨的人也轻松掌握的系统。这个系统必须完全依据语音记录,而且容易理解。在将速记方法应用于书写系统,将元音记号插入辅音记号后,柏格理先生与他的助手发现问题可以解决了。辅音记号比元音记号更大,音调标示在后者与前者的空隙间。
现在已有数千名苗族人可以读书写字了;这个有魄力的教会为该民族做出的贡献,绝对是难以估量的。当我前往那些允许我进入的苗寨时,只消经过十分钟指导,我就可以起身与他们一同演唱他们自己的赞美诗,阅读他们的福音了。在这以前从未奢望过阅读的苗族妇女,如今也逐步掌握了上帝圣言;易于理解的文字,令她们几乎立刻就能读懂十字架的故事。这当然只是传教事业在中国的杰出成就之一。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情感与宽阔胸怀都极具魅力,而且与汉人之间差异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一点是相同的。
苗民送别丁格尔,右侧戴斗笠者为柏格理
说起在苗族中的传教,作者对圣道公会极有发言权。他们以东川府和昭通府为大本营,非常值得赞扬。我在当地逗留期间,几位传教士对我这个完完全全的外人非常亲切。我将终生感激该教会的两位传教士,那就是东川府伊万斯夫妇,他们曾在我离开昭通后一或两周时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将在之后的章节详细叙述。那还是圣经公会的旧时代——自发前来的工作者尽管并非教会的正式成员,却遍及全中国,相较他们,再也没有谁能凭着这么低的薪水在工作时拿出这么高的热情了——那也是传教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
苗族大众是他们古代先王的后裔们的农奴,先王们都是地主,苗人是佃户。1905年苗族人听到了福音,于是开始听取布道,每次要有数千人一同前来,还有人直接去了宣教屋。结果他们的行动令汉人心生疑虑,由此引发了大量暴力与私刑事件,有一次甚至险些发展成了重大危机,好在迅速被镇压了下来。头领让地,苗人交钱;苗人还自己建了一座足以容下六百人的小教堂。一年后,每次有一千人挤在他们朴素的小教堂里;到了1907年,已有将近六千人成为或即将成为正式成员,从那时起,传教事业也就稳步发展了。
在我经过该地区时,当地的工作正由 H. 帕森斯牧师一家负责。下面我会讲到的这些有趣细节,均有关如何管理这般宽广的传教区域,为了获得它们,我在帕森斯处客居了好几个月,因此欠了他们不少情。帕森斯先生的工作由他亲切和蔼的太太辅佐,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苗语。帕森斯太太定期为几百名苗族人举办集会,而且经常与她的丈夫一起旅行;中国传教是一个女性工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体系,它的智慧,便是由她与其他人的杰出成就证明的。
原文刊载于“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基督时报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