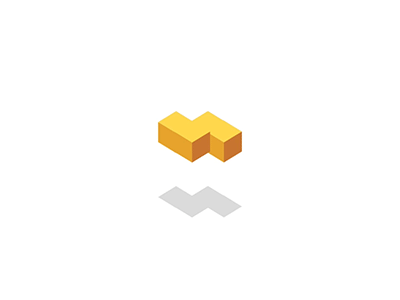编者按:圣诞季即将来临。本刊转载刊出“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回顾今年10月份一次德国之旅游记中几篇对于基督教与宗教改革有很多的探讨,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本文为就士游随团专家陈浩武教授与李筠副教授在就士游“德国宗教与哲学之旅”的讲座实录节选,未经两位教授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主题:“教皇革命及其敌人”
时间:2016年11月3日
地点:德国.康斯坦茨
主讲:陈浩武教授、李筠副教授
教皇革命及其敌人(下)
——南德十日行记(14)
主讲 | 李筠
随团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上接昨日内容)
“叙任权之争”的结束
“卡诺莎之辱”使得教皇与德国的梁子没法解了。所以我们看整个德国史,对教皇都是恶感,把教皇写得很坏。
西方的斗争就是这样,四处相斗,也挺狠的。但是,格里高利七世如果把亨利四世干掉了,谁来做皇帝?好吧,原谅你了。回去乖乖承认我那二十多条的“教皇如是说”。但亨利回去又贼心不死,这次把后院打理好了,纠集一帮兄弟,然后再领兵去罗马。
从“教皇如是说”开始,罗马教皇的继任者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任者就搅和在一起,互相打,一方想把它撕了,一方又要保住它。于是,教皇利用德国诸侯牵制皇帝,就成为一个常态。因为只要不把他的后院搞乱,他就会立马带兵翻过阿尔卑斯山把你给灭了。所以教皇保持德国的混乱,是他生存的必需。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人特别恨教皇的原因,英国、法国在16、17世纪,作为民族国家已经很像样子了,而德国人在1800年被拿破仑揍了的时候,还没找着感觉,落后了三四百年。这和教皇深深地把手伸进德国,就不让你们德国好,是有关联的。
沃尔姆斯的路德纪念碑 1902
最后,斗得没有办法,双方也就妥协了,签订了《沃尔姆斯协定》,皇帝和教皇分享权力。虽然没有初始“教皇如是说”里那么大的教皇权力,但总体来说,教廷、教皇、教会的优势地位,就被这个协定落实下来了。好比原来是九一开,双方斗法斗了七八十年甚至一百年,签订《沃尔姆斯协定》以后,基本上就变成了六四开,教皇还是相对占优势的。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沃尔姆斯协定》看成“叙任权之争”的初步结束,但是皇帝和教皇斗法的局面并没有结束,一直贯穿了下来。我们大概要强调这么几点:
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始样板
第一个,教会的理性化、国家化,是一个重要的进程,它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始样板。英国、法国和其他公国的国王就是瞄着它去建造的自己的国家。如果你要跟皇帝抗衡的话,你这个政治组织如何找到力量,其实是一回事,钱从哪里来?如何管理?因为没有军队,所以外交就更重要。总体上,就要围绕法律来做一些事情。我们现在熟悉的司法体系大概是一个上诉的结构,两级或者三级上诉,这个东西在罗马法里出现了原型,而把它做成一个体系的,则是教会。教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首席大法官。所有案件,不论英国人法国人,要告你们国王,大主教那里不算终局,可以来教皇我这儿,我替你们做主,所有的王侯、大主教,我都可以让他们服从我的判决。上诉体系就逐渐归拢了,政治管理就出现了一个理性化的进程。
那么你要上诉呢,就得有法,得知道听谁的规矩。“教会法”的法典化,是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英国法、法国法、德国法,就是学的教会法,因为聪明人都在教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教会法家格拉提安,写了《格拉提安教令集》。
教会法大概就是历代教皇发布的教令,类似于“教皇如是说”,只要他写出来发布了,就是正式的教会法,凡是基督徒,全都要遵守。但是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就容易乱了,于是交由法学家来整理,把它变成一个体系:第一层的道理是什么,第二层的道理是什么。就像我们在魏玛讲基督教的教义学一样,逐渐归拢为一个合理的体系。
要把一团乱糟糟的法令理顺了,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格拉提安初步做成了这个事情。后来人学着他的办法,增补了三本教令集,公元13世纪,将四本合在一起,成了《教会法大全》,成为了通行欧洲的法律。它们不仅是有实际作用的法律,而且是各国学习的对象,怎么样把法律体系建好了,国王管理起来才有章法。所以西方法律重要的结构性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教会法》里。
罗马法复兴
大概在公元11世纪前后,“罗马法”也回来了。但是在欧洲,罗马法当时并不具有真实法律效力,它就是学院的教科书,不像教会法一样,写出来你们就一定要遵守。而这个罗马法是教授和学生聊聊,有什么道理赶紧弄出来,而对旁人是没有效力的,是一种学习材料。
为什么罗马法被捣鼓出来了?因为教皇和皇帝吵架,总得有根据吧?西方有一个很好地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就是“不承认没有权利根据的权力”,中文不好表达,我们用英文就比较准确:不承认没有“right”根据的“power”。也就是说,任何power,都要问一句“凭什么”?有什么样的right支持你这么干?这个power一定要坐落在right上面。所以我们说神学的、哲学的、法学的论证对于你掌握这个power就变得很重要。你皇帝到底有什么权利比教皇大?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
在教皇和皇帝长期的斗争中,理论斗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神学家、法学家都要替各自的老板到书里找依据,哪些东西有利于你?哪些东西有利于他?有利于你的我们怎么发扬光大?有利于他的我们怎么想办法驳倒它?所以西方的政治理论就特别发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初当然是教皇占优势,我们俩是以吵架定输赢,不是用拳头定输赢,如果我识字,我能读书,你肯定吵不过我,我都讲一套一套的,有什么典故,有什么根据,你只能干瞪眼,啥也说不出来。所以教会的“叙任权”之争一开始双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格局,教皇在理论上占尽了优势,皇帝一方基本上说不过。
以博洛尼亚为首的中世纪罗马法复兴,实际上最重要的政治动力,就是皇帝去罗马法那儿找根据,找帮手,因为在基督教系统里,在神学系统里要干过教皇,基本上是没有胜算的,必须找一个能抑制对手的东西。而且罗马法里有很多很多关于皇帝权力的说法——你看,罗马人早就这么讲了!这和神学那一套不一样。所以从博洛尼亚开始的罗马法的复兴,和我们一开始讲的教皇革命,实际上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方面、不同功能。
当然,罗马法复兴也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从政治上来讲,它和教皇革命的政教双方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
西方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定型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教皇革命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普遍的理性化,无论是讲神学、还是讲法学、还是讲哲学,都是要讲道理、讲逻辑的。政教斗法没有太久,大概在1270-1280年代,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就出现了。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一套东西和奥古斯丁的一套东西合二为一,一个庞大的几乎像法典一样的教义学就形成了。这里面成千上万条理论,没有任何的逻辑冲突存在,非常非常细密,理性化程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法学肯定更是要讲道理的,权利怎么往下推,谁拥有什么权利,违反了什么规定,上什么法院起诉,等等这样一套东西,法典、法院体系就都理性化了。
第二个,就是全面的规范化,无论是神学讲道理,还是法学讲道理,规矩越来越充分,不像是那个日耳曼从和森林里出来的、和神接的很近、脾气很容易暴怒、很随性的野蛮人状态。
第三个,就是西方社会一个基本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定型了。一边是教会,一边是世俗政权,谁也吃不定谁,通过教皇革命,就把这个结构坐实了。这个结构对于西方来说,是顶顶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教会被皇帝干掉了,最合理的结果,就是像拜占庭一样,大牧首成为皇帝的官员,基本上就是俄国的那条路子,沙皇的那种模式,那对西方来说就大不一样了。反过来,如果教会吃掉了皇帝,吃掉了国王,那基本上就非常像伊斯兰教的状态,宗教领袖比世俗领袖要高得多,很显然都不会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路子。
我们讲的中间道路,恰恰是谁也吃不掉谁。不断斗法的路子,才斗得出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实际上是有一种结构性的牵制存在。而西方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教会这个系统的存在。皇帝、国王就是想吃定对方,就是吃不下来,反过来当教皇强大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国王和皇帝吃死。
这里多说两句,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到后来世俗化了,因为教会在路德、马基雅维利这些人的攻击之下,坍塌了。到《奥格斯堡协定》一签订,教随国定,谁的君主,谁的信仰,统一的教会就没有了,对整个世俗王权的控制、牵制,就大大下降了,所以就出现过一段政权特别凶猛,没有人管得了、制约得了,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绝对主义君主的时代,比如说路易十四。这个结构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后来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等等,教会最后被社会取代,变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制衡的关系,在政治、国家、权力之外,始终有一套结构性的力量存在,且不被你吃掉——我就是要和你纠缠在一起,但是不成为对你俯首听命的那一部分。这样,政治、国家、权力才会处在一个我们想要的不仅是有限,而且是守法的状态。
所以说,教皇革命从政治学上讲,就是的二元结构的老模式形成了,先有教会对世俗政权的二元结构,才会有后来的社会对国家的二元结构。如果中世纪不存在前者,那就很难想象后者会出现了。
宪政革命不是"反封建"
最后一点,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政治进程的加速。教皇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早的榜样,无论是司法、财政,各种管理,法典的颁布等等,都成为英、法学习的对象。但在这里,首要的目标不是为了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绝对主义君主国家。以前我们讲的是专制国家,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用绝对主义来描述的,它的顶端就是“君权神授”,国王、皇帝的权力当然是来自上帝,这还用问吗?然后,它也不是胡来的,它的核心,是超越于法治之上的政治的帽子,就是国家理由等等,君主就是要捏住这个东西,领着这个国家往前走,接下来才有咨议会、顾问团,然后依靠法律来统治等等。路易十四做到了这个事情的顶峰,而他学习的对象就是教皇国。
绝对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初期的君国,依靠打仗,扩充领土。所以一旦教会坍塌,绝对主义兴起,整个欧洲就打成了一团。实际上宪政革命就是对这种国家的矫正,而不是什么反封建。封建领主早就被一些想要说一不二的国王干掉了:外部没有教会制约它,内部诸侯也制约不了它,它必然就会膨胀得很厉害。所以说,宪政革命主要是革的这些君主的命。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的是,政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在教皇革命引起了教皇国成为一个非常接近现代国家的绝对主义的君主国,然后英国、法国赶紧学习它,利用司法、财政、军事等等方面集权,形成一个战斗的机器,才能够在列国并存中打赢其他国家。但是这条路一旦滚进去,就出不来,除了打仗就是打仗,提取民脂民膏,所以要杀入这个战车,只有从内部,国王根本就不是军权神授,这个国家就应该是人民的。
西方如何走入现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和前天浩武老师讲的相呼应,教皇国成为一个绝对主义国家,它当然就是腐败堕落的。他要建宫殿,要养军队,这个钱从哪儿来?即便不是奢侈腐败,他也得去收钱。康斯坦茨公会后,也就是1418年以后,本来已经很具规模的教皇国继续往绝对主义君主国方向滑落,变成列国竞争中的一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欧洲共主的地位,而是和英国国王、法国国王、皇帝、各种公爵纠缠在一起,纵横捭阖,成为他们之间的角色之一。它要养一只和法国一样的军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外交穿梭就特别频繁。
正是因为教皇深深卷入了世俗政治,跟大家一起玩,以前高高在上、从精神层面俯视指导世俗领主和国王的格局,实际上已经破掉了,它的理想没有了,沦落到同大家一样的世俗角逐当中,腐化堕落当然就非常迅速,甚至是加速度。不到一百年,路德就贴出《九十五条论纲》,马基雅维利就写出了《君主论》,反对教皇。几乎所有国家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烂,就是被教皇搞坏的,教皇甚至成为欧洲共反的一个对象。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格里高利七世1071年颁布“教皇如是说”的时候,是一个正向的能量,要把欧洲打理得非常强有力,大家知道政治的方向,一起跟它走;但是很快,因为堕落、腐化,它成了被攻击、被批判的对象。于是,新的时代,以路德和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现代政治产生,西方就这样走入了现代。
- 未完待续 -
基督时报蒙允转载自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微信公众号,不拥有版权。